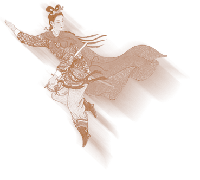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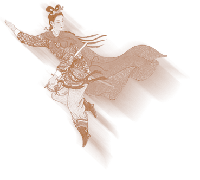
|
周惠娟 序:新說者言
百行以孝為先,「俠女」與「顧」生皆侍母至孝,「俠女」為「生」產子皆因有感於恩人「顧」生命短無壽,不能伴母以終老,若有子延續燈火,當可免「生」母晚年孤苦無依。 《俠女》除了孝與義之動人章節,其中有關男主人翁孌童之行為,「蒲」氏沒有以異端而視之,其持平態度較現代人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全篇的神韻在於「蒲」氏對人物性格的刻劃,「俠女」冷傲重義,「顧」生孝順多情,故事的結局沒有道出「俠女」到底是人或是靈通之物。 按:古文之「孌童」是指與同性之美少年有越軌行為,並非戀上兒童的意思。
9 - 8 - 02 |
||||||
|
「顧」生,「金陵」人也,精藝術善詩書,誠博學多才者,惜家境貧窮,欲離鄉另覓前途,「生」以母親年事已老,不願離慈母膝下。平日「生」以替人作詩寫畫,賺取酬金以活生計。 「生」行年二十有五,礙於家窮仍未置家室。 位「生」對戶一所舊房,無人居住多時,最近來了一老婦及一少女,把房子租下入住其中。「生」以新鄰居家無男子,故未有向其請益姓氏。 一日,「生」偶然外邊回府,見女郎自母房走出,望之,女郎年約十八九,秀氣迫人,舉止文雅,如此清靈美態,真的是世間罕見。若有,定然難得與眼前人相比也。望見「生」回房,女郎並無回避,不若一般女兒羞態。只可惜容顏冷漠意氣凜然,沒說一句話便逕自走矣。 母曰:“是為對戶女郎,剛才過來求借刀尺,方知其亦只有一母相依,惟以外表觀之,此母女二人不似貧窮人家,故追問為何仍待守歸中,女郎告之因侍母以終老為理由,故不思婚嫁。” 「顧」母洞悉「生」留神於女郎,故續告「生」:“明日當拜會其母露些口風,看可有作親家之意否;倘若要求不高,兒可代之奉養老母天年。” 翌日,「顧」母往登門造訪,女郎之母乃耳聾者,「顧」母環顧周圍,發覺一無所有可謂家無隔宿之糧。 「顧」母大聲問婦何以為生,老婦答之靠女兒十指針線過活。 「顧」母便與婦共同便飯,並將來意表明,徵求婚嫁之事,老婦有意接納提親,遂轉向女郎徵求意思,女默不作聲,看其表情似是不置可否。
母拜辭歸家,見「生」即將情形詳細陳述,「顧」母以懷疑語氣曰:“女郎恐是嫌吾家窮困乎?看她不言亦不笑,真箇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,端的是奇女子一名也。”一日,「顧」生埋首案頭,有一少年男子前來求畫,看他姿容甚美,面滑如童子,而神情意態甚是輕佻。「生」望之乃陌生人也,遂問其何方來客,少年答曰:“隔鄰村人。” 從此或三日或兩日必來一次,二人漸見熟落,但見少年語意調笑,「生」狎抱玩弄,少年亦不拒絕,最後竟作假鳳虛鸞矣。由此二人往來親暱勤勤。有一回,女郎經過,少年目送之,而眼瞪口呆,急問「生」女為何人;「生」答曰:“鄰家女子。”少年曰:“艷麗如此,神情為何如斯令人生畏。” 過了一些時日,「生」進母房,母曰:“是剛才女郎來這乞求一點白米,「女」云無米可炊已幾日矣。此「女」侍母至孝,可嘆貧窮如此,兒要體恤之為其周轉之。” 「生」遵從母言,立刻背起斗粟米糧登門表達母意。女郎馬上收受所贈,亦不曾向「生」說句謝話。 日間女郎常來「生」家,見「顧」母縫衣服鞋襪,女郎必替「生」母縫紉,出入房間打掃明淨,其行為舉止恰如媳婦。 「生」越是對之尊重有加,「生」每次賺得賣藝錢,必分一份其母,女郎從沒說一句感謝之詞,「生」亦習以為常,見怪不怪也。 如是者又過了好些光陰,「顧」母陰處忽長起毒瘡,日夜奇痛嚎哭大叫,女郎過來侍候榻前,為「生」母洗瘡敷藥,每日必替換藥三四次。 「生」母見「女」如此服侍,深感不安,女郎態度溫柔,看其表情真箇是甘之願之,遂不厭其穢也。
「生」母曰:“唉!如何有媳婦孝順如親生女兒,侍我以終老也!”說罷,不禁悲哀咽哽。 女郎安慰曰:“令郎大孝,勝我等寡婦孤女百倍矣。” 「生」母曰:“床邊瑣碎等事,豈孝子所能有此細意,況且老身年事已高,大去之日或在旦夕間也。然而最遺憾者,乃為香燈繼後擔憂耳。” 談話間,「生」進入。「生」母泣曰:“我家虧欠娘子甚多,汝毋忘記回報大德。” 「生」聽母言,即俯首拜謝之。 女郎曰:“何須如此,君敬我母,我何曾謝汝,我敬君母,君何須謝我焉?” 「生」聽得此言,益增敬愛。「生」每欲表達愛慕之情,然女郎舉止生硬,其凜然冰冷,使人不敢輕舉妄動,莫說是一聲調情話,正是可望而不可即也。 一日,女郎自「生」處返家,「生」目送之,女郎忽然回頭對「生」嫣然一笑,端的是上天賜福,「生」喜出望外,不加思索馬上隨尾追去進入女郎居室。 「生」情濃如火復挑逗之,女亦不作拒絕,「生」再索之,女遂欣然與「生」交歡。一番雲雨過後,女郎告戒「生」曰:“事可一而不可再!” 「生」不以為意,沒有回應女郎所說。「生」回家,翌日「生」往約會之,女郎竟厲以顏色,遂不顧「生」而去。 如是者,女每日頻來探「生」母,偶然與「生」相遇,並未以厲色對「生」,亦無冷詞相向。「生」以為可將進一步,那曉得略作親暱之舉,女郎馬上變得冷若冰霜,「生」只得以君子禮待之。 忽然一日,正當無人之處,女郎曰:“日前來此之少年是誰也?”「生」告之少年來歷。 女郎又曰:“彼舉止輕浮,竟對妾多番態度無禮,惟念此人與君有親暱關係,故置之不理,請方便轉告,如復犯此,其不欲生還也。” 不久,少年來找「生」,「生」告之以女郎所囑,且警告曰:“子必慎守行為,此女子不可胡來侵犯。” 少年曰:“既之不可侵犯,君何又與為之?”「生」謂絕無越軌之事。 少年又曰:“如君與女子無親密所為,然猥褻之語,何以重覆告與君知之哉?”「生」不能作答,少年曰:“亦煩君寄語,勸她此假惺惺之態,還是少作為妙,不然,我將其所作四處張揚散播。”「生」見少年如此無賴,氣憤甚,面色登時大變,少年亦沒趣離去。 一晚,「生」獨坐房中,女郎忽然來到,笑曰:“我與君情緣未斷,唉!真箇是天意也。”「生」狂喜,一手把女郎緊抱於懷,忽然聽見步履凌亂聲音越趨越近。兩人聞聲驚起,則見少年推門進入。 「生」驚問:“子來為何,竟如此無禮?” 少年笑曰:“我來觀賞所謂貞潔之人耳!”望向女郎戲曰:“如今不怪人對汝輕薄耶?”女郎登時氣得眉豎臉紅,默不作聲,只見女郎急急翻起上衣,露出一革囊,颼一聲快響,應手而出為一尺許長之晶瑩匕首也。少年見之,大駭,慌忙逃走。女郎直追出戶外,四顧張望,竟渺無一人。 女郎連以匕首望空拋擲,匕首穿雲而上.所到之處竟鏗然有聲,但見寒光閃閃,一道長虹劃天而過。 俄頃間,一物從天墮落,及地面,發出轟然聲響。「生」急忙以燭照之,則見一頭白狐已是身首異處耳。「生」大驚,女曰:“此乃君之孌童也,彼與君勾搭,我固恕之,奈何其不顧警告,乃其不欲生也,與人何由。”說畢,收刃入囊。「生」摟女入屋,女郎曰:“剛才被妖物糾纏,如今意興盡失,請作忍耐,妾明晚再來會君。” 女郎出門逕自離去。「顧」生無奈惟有等待。 次夜,女郎果然來矣,「生」情急也,遂與女郎銷魂燕好。情事竟畢,「生」問女郎是何法術,女郎答之:“此非君所應知,惟所有事必須守秘慎言。若洩漏,實非君之福也。
「生」求女郎下嫁之。 女郎應曰:“今與君同枕席,又為君提水作家務,若非君婦又是何人?如今己是形同夫婦矣,何必復言嫁娶之事哉!” 「生」曰:“是否嫌棄吾乃一介寒生耶?”女郎曰:“君固貧,然妾富耶?今宵嫁與君,正是以君貧窮者耳。” 臨行又叮囑曰:“苟合之行,不可以常為之,若來,我自來,不當來,勉強應知無益。” 往後,每逢與女郎相遇,「生」欲與之私語,女郎總動輒走避,不欲與「生」交談。然「生」之衣服起居,燒飯茶水,皆悉心料理,不失為「顧」生婦也。 如是又經數月,女郎之母死矣,「生」竭盡所能為其籌錢殮葬之。 女郎從此獨居,「生」猜想「女」正當孤寂無聊,也許有機可乘,便於夜靜爬牆進入。「生」隔窗頻呼女郎,狀甚多情。可是頻呼不應,往裡面窺,只是房空無人,遂懷疑「女」與他人有約。臨夜,「生」又復往之,望去一如昨夜,「生」遂將玉佩掛於窗間而去。 翌日,二人相遇於「生」母房中,「生」一言不發,獨自往外邊走,而「女」尾追隨之曰:“君疑妾有新歡耶?人各有難言處,事有不可告人,今欲使君無疑,當知不可以,惟一事煩君急為解決。” 「生」問何事。「女」曰:“妾懷孕已八月矣,恐刻秒臨盆。而妾未嫁君,身份未明,今為君產子,惟不能為君哺育,可秘密告老母,為兒覓一乳娘,偽稱收養我兒為義子,切勿言為妾所生可也。” 「生」承諾,回家稟告母知,母笑曰:“異哉此女,下聘娶之不願,如今竟眷顧我兒,私為我家延繼香燈焉!”母依女郎安排,照其所囑準備育兒等事。 轉瞬月餘,女數日不出門,母疑為何事,遂往探望,但見門庭緊閉蕭條寂寞。母扣門良久,方見「女」蓬頭垢面自內而出,女郎啟門讓母進,又復把門緊閉之。 母隨入內,則見嬰兒之聲呱呱在床叫嚷也。母驚問:“何時誕下嬰兒?” 女郎答曰:“才出生三日。”母急忙解開繃布視之。是為男嬰也。見得此子面兒豐滿,額頭高度。大喜曰:“兒已為老身產下孫子矣,然汝伶仃一人,又將何所付託?”「女」曰:“妾有隱衷,不敢坦言相告,請臨夜可把兒抱去。”母不便追問,心甚憐愛,及家門,母告其子一切事,母子二人皆以女郎異行,惘然無所知之。入夜,逕往女郎居處,把子抱歸。 數日過去,一晚半夜時分,「女」忽然推門而入,手提革囊,笑對「生」曰:“大事已了,從此便與君別!” 「生」急急細問其故。「女」曰:“君為我養母之德,妾刻刻不能忘懷。一向對君說「可一而不可再者」,妾以相報不在與君床笫之交。惟妾以君貧難以成婚,與君相好,乃為君延一繼後,本以為一次之交歡當成孕,不料月事復來,以至破戒再與君相好。如今已報君大恩,妾願已了,當無憾矣。” 「生」望女郎手中革囊,好生奇怪曰:“囊中為何物?”「女」曰:“仇人之頭也!”「生」聞之,走近窺看,見得人頭鬚髮交纏,而面目血肉糢糊。「生」驚駭萬狀,細問原因。 女郎曰:“一向不與君言者,乃因怕機事不密,恐有外洩。如今事情已成,不妨如實相告。妾為「浙」人,父親官為司馬,不幸為仇家陷害,慘被抄家。妾背負老母逃脫,一直隱瞞姓氏,埋藏身份已三年矣。何以不馬上雪此仇恨,此因老母猶在,母逝矣,一塊骨肉又在腹中,故拖延甚久。” 「生」答曰:“為何深夜幹之?” 「女」曰:“深夜出動,無非因仇家門戶未熟,恐有訛誤者耳。” 女郎說畢,出門欲去,臨行又囑「生」曰:“妾之所生,請好好教養,君福薄無壽,此兒可光亮門楣。現已夜深不可驚醒老母,我去矣。” 「生」不知所措,見女去,方悽然欲問所往何處,然「女」一閃如電,瞥眼間遂不見去向。「生」嘆息悽悽,呆然木立,如喪魂魄,「生」傷心甚甚。翌日,將女事蹟一 一稟告母知之,母子二人嗟嘆此異數奇逢。 三年過去,「生」果然卒。子剛屆十八之年,舉得進士,以孝傳聞,如今猶奉祖母以終老云。
「異史氏」曰:「人必室有俠女,而後可以畜孌童也。不然,爾愛其艾豭,彼愛爾婁豬矣。」 新說者言:俠女者無名氏也,故事女主角姓甚名誰作者從沒提及,這是「蒲」氏為人物塑形的巧妙,小說成功地將女郎之情義與俠義之氣躍然於文字交替之間,女郎之美是屬於靈氣迫人正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,她的情背後包含深深的義。 俠女愛「顧」生嗎?作者沒有明確交待,但從一則微小處卻又感覺女郎似是無情卻是有情,《新說》第三節──(一日,女兒自「生」處返家,「生」目送之,女郎忽然回頭對「生」嫣然一笑,端的是上天賜福,「生」喜出望外……)須然女郎為了還「顧」母之大恩,亦有感於書生之相助,因知書生短壽而為其生育,好讓「顧」家有後「顧」母亦老有所依。 惟對生一笑嫣然若果無情豈會笑意如斯?女姓是感性之物假裝有情不會有嫣然笑臉,更何況是性格傲凜之女郎? 「蒲」氏其實多處帶出女郎非無情也只是另有因由,《新說》第五節,女郎曰:(“今與君同枕席,又為君提水作家務,若非君婦又是何人?”) 然而,女郎是何許人氏?「蒲」氏最後只交待女郎乃「浙」人,父親官為司馬,因被仇家陷害抄家,女郎背著老母逃脫死難。這裡更加強了女郎身份的神秘,女郎之存在是為了侍候母親終老,俟母親死後立即把仇家除掉,然後與「顧」生作別,只見女郎電光一閃便失去蹤影。女郎是人?是鬼?是神仙?惟肯定不是女狐,在「蒲」氏小說中凡狐之兒女皆有狐之動靜,但女郎之子並無此相。 若然非女孤,但見女郎身手非凡來去如神鬼之無形無影,女郎難道是孝感動天求道得道,並得以返回陽間照顧其母直至母死? 如此推理,女郎實在死去多時矣! ──完── 17-6-2002 網內所有文章的版權,全屬網主擁有, 未經受權許可,不可作任何形式的轉載。 |
||||||
 返回主頁 返回主頁 |